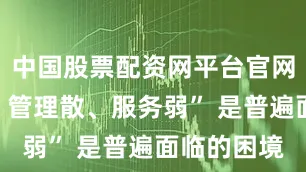“功臣就该被杀?那谁还敢替你打天下!这话确实是一点毛病都没有,只不过,时间节点不同,那么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。”

在古代来说,不管是谁,都很难逃过,免死狗烹,鸟尽弓藏。即使是兵仙韩信,也同样如此。说到这里,你肯定听过“胯下之辱”“背水一战”,也大概知道他就是“兵仙”,可你未必清楚,他最后是怎么死的:不是战死,不是病亡,而是被人塞进麻袋,用竹签一根根扎死,天不能见、地不能踏、铁器不能碰,连死,都不配死得像个“人”,你敢相信这是兵仙韩信的下场?
更让人心寒的是,把他骗进宫门的,不是敌人,是他最信任的恩人、当年冒雨追他几十里地的萧何。
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职场剧?老板创业时把你当兄弟,上市后第一个裁的就是你,并且还直接把你除掉。但是现实比剧本更狠,韩信连“体面离职”的机会都没有,直接被物理清零,因此很多人为韩信鸣不平。

韩信年轻之时,真不是一般的惨。家里穷得叮当响,天天在淮阴街头晃悠,靠一位漂洗衣服的老太太接济才没饿死。有一次,一个屠夫当街拦他,冷笑:“你不是佩剑吗?要么砍我,要么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!显然当时的韩信连屠夫都在欺负他,根本不把韩信当回事。”
如果换成是你,恐怕是早就拔剑拼命了。可是韩信盯着屠夫看了好一会儿,一言不发,弯下腰,钻了过去,这便是胯下之大辱的典故,如果当时韩信拔剑,恐怕结果就不一样了,要么死,要么残。
当时很多街坊笑他窝囊,说他没血性。可后来大家才明白:他不是怂,是格局太大。街头那点脸面,在他眼里,连一粒尘都不如。他心里装的,是山河万里,是千军万马。

乱世一起,机会就来了。他先投项梁,项梁战死,又跟了项羽。可项羽这人,勇猛归勇猛,就是刚愎自用。韩信给他献策,说“打仗不是光靠蛮力,得收民心”,结果人家眼皮都不抬,只让他干个传令的小官。韩信心凉了半截,转身投奔刘邦。
可刘邦最开始也没把他当回事,只让他管粮草仓库。韩信觉得没奔头,默默收拾行囊,准备走人,打算再看看情况。就在韩信准备打退堂鼓之时,萧何出现了。

这位汉初第一文臣,听说韩信要跑,鞋都没穿好,连夜追出去几十里,硬是把人劝了回来。回来后,他直接拍着胸脯对刘邦说:“你要想争天下,非韩信不可!别人都是将才,他是帅才!正所谓,千军易得,一帅难求!”
对于萧何之言,刘邦也是半信半疑,但还是给了排面,刘邦下令:筑高坛、设仪仗、全军列阵,正式拜韩信为大将军。那天,整个汉营都炸锅了:一个管仓库的,怎么突然成了三军统帅?
可韩信一出手,所有人都闭嘴了。
他暗度陈仓,神不知鬼不觉打回关中,章邯这些秦朝老将被打得找不着北;
井陉口一战,他让士兵背水列阵,几万新兵硬是干翻赵国二十万大军;

后来平定齐国、十面埋伏围项羽,逼得西楚霸王在乌江自刎……
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韩信,刘邦最多在汉中养老,根本坐不上龙椅。
按常理,这种开国元勋,怎么也该封王拜相、子孙享福吧?但是事实上呢?却并非如此。
刘邦当上皇帝后,眼神变了。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异姓王,在他眼里不再是兄弟,而是隐患。燕王臧荼刚有点风吹草动,就被他亲自带兵灭了;赵王张敖手下人搞刺杀,哪怕他本人毫不知情,照样被废为庶人;梁王彭越更惨,就因为称病没出征,被扣上“谋反”帽子,剁成肉酱,分送给各地诸侯“观摩学习”。

韩信看着这一幕幕,心里直发毛:下一个,是不是就轮到我了?
其实他早该学张良。张良多聪明?功成身退,隐居山林,修道养生,谁也不惹。可韩信偏不信邪。他觉得,我功劳这么大,刘邦总得给我留点体面吧?于是称病不上朝,还当着刘邦的面说:“陛下最多带十万兵,我嘛,多多益善。殊不知,韩信这话,早就触碰到了刘邦的逆鳞。”
这话要是朋友间吹牛,一笑就过了,但是韩信却忘了,他这是在和刘邦讲话。可在皇帝耳朵里,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:你比我强?那你是不是也想坐这个位置?由此一来,刘邦想不整治韩信都不行。

后来陈豨在代地造反,刘邦亲征,点名让韩信随行。韩信又推说生病。没过几天,就有人举报:韩信和陈豨密谋,要在长安里应外合,发动政变!消息很快传到了刘邦耳中。
吕后一听,吓得手心冒汗,韩信要是真的来,还真不好对付。她立刻找萧何商量:“这事儿怎么办?”
那一刻,萧何的内心,怕是翻江倒海。一边是救命知己,一边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——彭越的肉酱还在诸侯案头上摆着呢。他要是不站队,萧家上下几百口,明天可能就没了。
思来想去,他咬牙做了个决定:帮吕后,骗韩信。

他亲自登门,语气诚恳得让人没法怀疑:“陛下打了胜仗回来,满朝文武都去庆贺,你就算病着,也该露个面,表个忠心。”
韩信信了。他太信萧何了。毕竟,当年是这个人,在他最落魄时拉了他一把,把他推上神坛。
可这一次,神坛塌了,底下是刑场。
韩信刚踏进长乐宫钟室,埋伏的武士一拥而上,麻袋罩头,拖进暗室。吕后连审都不审,直接下令:“用竹签刺死,不准见天、见地、见铁。”——这不是怕他冤魂作祟,而是要彻底抹去他作为“人”的尊严。
一代兵仙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没了。更惨的是,他死后,三族尽诛,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。
而萧何,站在远处,只冷冷吐出四个字:“为国锄奸。”

这话听着正气凛然,可细品全是苦涩。他不是冷血,是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,情义抵不过活命。他必须选边站,否则全家陪葬。这不是道德选择,是时代给所有功臣设的死局:要么踩着别人活下来,要么自己死。
现今回过头看,韩信的悲剧,从来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,而是他生错了时代。在一个没有制度约束权力的社会里,功劳越大,越像靶子。因为你越强,皇帝就越睡不着。
刘邦要的从来不是“能臣”,而是“听话的臣”。韩信太能,又太傲,还总觉得自己该被尊重。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,皇权早已把“尊重”标好了价码,那是恩赐,不是权利。
所以,别再说“韩信不懂政治”了。他不是不懂,是不屑玩那种“自污保命、装疯卖傻”的把戏。他相信自己的价值,也相信君臣之间该有基本的信任。可惜,他高估了人性,低估了权力的冷酷。

长乐宫钟室里那袋血肉模糊的尸体,不只是韩信一个人的终点,更是整个帝制时代功臣命运的缩影。没有规则的权力,就像一头没有缰绳的野马,迟早会把曾经最忠诚的骑手,踩进尘埃里,对于此,您怎么看呢?
启恒配资-配资查询114-股票配资门户网-全国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深圳股票配资平台一名探访过格蕾塔的瑞典外交官员透露
- 下一篇:没有了